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评论学会第六届年会活动系列报道——居其宏教授访谈录
时间:2016年11月13日
地点:音乐学院会议室
杨柳成:居教授您在音乐评论方面颇有建树。那么,请问,您认为作为一个合格的音乐评论者,需要具备哪些素质?
居其宏:作为专业音乐评论的乐评人,就不是像那种业余的评论人一样写一点随感,写一些散文式的文章。要有一定的专业含量和学术含量,有一定的思想高度。一是要热爱音乐,二是要学过音乐。要知道音乐艺术的基本规律和它的特殊性。另外一个就是要多听音乐。古今中外最著名的音乐作品,都要好好听,领悟其中的奥妙。要以历史上最好的作品来作为衡量尺度。感性经验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。而且最好是要到现场听音乐会。因为,听唱片毕竟没有听现场音乐会那样有真切的感受。还有要多读书。音乐评论,基本的生存方式就是用文字来表达作者的所见、所想、所思。文字的表达,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人文素养包括历史的、哲学的,美学的。要多读好书,读经典的书。除了一般的音乐评论著作以外,还要读一些大美学的书。包括歌德、黑格尔、马克思,恩格斯、毛泽东等人的一些东西。也对我们的音乐评论是有好处的。他们对艺术作品的切入。包括恩格斯所说的,历史的、美学的、音乐工艺学的三个维度,对音乐作品进行评价。对这些,我们都要学习掌握。这样我们通过多练笔,多思考,多实践,多老师请教。天长日久,日积月累,必有所成。这是有一个过程的。如果真的是热爱音乐艺术的话,就应当把许多课外的时间,花到读书听音乐上面去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,也是我的基本经验。必须要多读书,多听音乐,多看乐谱。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能够让人信服。有一定的思想深度,分析音乐技术的手段扎实,才能说是内行。
杨柳成:您不仅对音乐评论上面,很有建树,而且对中国歌剧方面也很有研究。请您对近年来中国当代歌剧创作进行一个评价。
居其宏:对于歌剧人们有一个说法,那就是“歌剧是音乐艺术王冠上的宝石”。我还要说的是:在人类创造的各种艺术形态当中,它是一艘航空母舰。高度精密,高度复杂,需要把所有的文学的、音乐的、美术的,包括形体语言,包括声、光、电,全部精密的组合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之上。所以它非常精密,非常复杂,是高度综合性的。研究歌剧要比单纯的研究音乐呢,又要困难一些。它的知识储备,它牵涉到的学科更加复杂。二十世纪初以来,从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年之久了。在这其中产生了非常多的好作品。但也有些问题。近年来,尤其是新世纪以来,中国歌剧也不是没有好的作品。但是主要的主流,还是采用西方正歌剧的形式,结合中国的故事、中国的人物,包括有些自觉采用中国传统音乐的音调、音乐元素、思维方式来写中国的当代的歌剧。如果有100部中国歌剧的新作品,其中有80部这样的作品。
当然还有另外一些继承《白毛女》传统的(民族歌剧),除了向西方学习基本表现体系,比如说它的管弦乐队、各种声乐形式(重唱、合唱、宣叙调、咏叹调)等形式之外,还有跟西方歌剧不同,也与中国向西方歌剧学习的正歌剧不同,就是借用中国戏曲的结构和思维,来写作主要人物的核心咏叹调,这是中国民族歌剧的最大的特点。我们听过的,还留有记忆的那些如:《白毛女》、《小二黑结婚》、《红霞》、《洪湖赤卫队》、《江姐》到新时期的《党的女儿》、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都是一脉传下来的。这一脉,在过去的五六十年代是主流。这些歌剧广大人民群众是熟悉得很,能唱其中的很多调子(咏叹调),就算不会唱,他们也很爱听。包括一些像主题歌一样的东西,比如说《洪湖水浪打浪》、《红梅赞》等歌曲在当时都很流行。这一脉到了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。由于西方现代思潮的涌入,民族歌剧当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。有些问题没有解决,所以新时期有很多作曲家就不愿意再走这条路,就开始走西方那条路,所以正歌剧就多了起来。当然也有一部分人继续走(民族歌剧这条路),像总政歌剧团王祖皆、张卓娅这两位作曲家,写的《党的女儿》和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一脉相结。去年《白毛女》创作七十年,文化部、中宣部又把《白毛女》歌剧重新排演,在全国十个城市巡演。然后又有北京电影学院,又拍了一个3D舞台艺术片《白毛女》,雷佳演的。虽然3D舞台艺术片我不太喜欢,但是这个歌剧,还是很好的。
当代很多歌剧的剧作家、作曲家心态十分浮躁,他们写的剧本戏剧品格很羸弱很薄弱,就是没有戏。什么是歌剧?瓦格纳对歌剧有一个权威的概念。歌剧是利用音乐展开的戏剧。本质上,是戏剧,只不过它的表现手段不同,它是以音乐来展开的,才叫歌剧。用身体和舞蹈语言展开的呢?它就叫舞剧。用语言和身体来展开的,那就叫话剧。这就不一样了。当然,中国戏曲王国维有很经典的定义:以歌舞演故事。歌舞是他的手段,要演成故事,故事要有情节,有人物有形象,有冲突,有发展,有低潮,有推进,有高潮,最后矛盾解决。现在我们的剧作家,这方面很差,所以,中国歌剧和音乐剧的剧本要比起中国戏曲,尤其是地方戏曲的文学剧本来,它们的质量还是差的很远。我们应该好好向戏曲学习,尽管它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戏曲,都是中国的新创作的戏曲。比如说豫剧《焦裕禄》,这也是一个主旋律的题材,按道理来讲应该非常不好写,但是人家写的非常好,非常感人。这就不但要有高超的政治责任感,要把英雄人物写好;也要有崇高的艺术责任感,一定要通过最美的艺术形式,把这个人物的形象在舞台上刻画出来,树立起来。让人感动的一个人,让人感到他的思想的崇高,他的人格的伟大,然后向他学习。而不是做一个政治的传声筒,简单化。
像冼星海,伟大不伟大?伟大!写了很多好作品。要不要写?要写,怎么写?写冼星海一下子写了好几部。像广州有一部叫《烽火冼星海》,中国歌剧舞剧院也搞了一部,总政歌剧团也搞了一个冼星海,叫《天下黄河》。三部作品,基本都是围绕主旋律去的。应该向《焦裕禄》剧组学习。这个人物你要把他人格上最伟大的地方,包括对《黄河大合唱》的诞生,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触发了他的艺术灵感,要把他的这个写出来。概念化、一般化,如果这么写就不行了。东西写出来,结果没有感染力,不是正能量而变成了负能量。如果只是口号式的、简单的配合政治任务,这怎么能行呢。恰恰在中国歌剧、音乐剧舞台上这种东西太多。
歌剧创作应该真正深入到符合歌剧艺术规律的,真正深入到人物内心深处的。把握它的独特性:“这一个”。恩格斯说什么,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以外关键是要写出“这一个”,这个人跟别人不同。独特性,他的独特的性格,戏剧矛盾当中的他的独特的行为逻辑,他的心理依据。这样的话才能刻画出他的伟大来。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好。还有音乐创作方面也是一样,有一些急功近利。作品写出来,演出的效果如何?作曲家基本没有关注,像是口水歌。虽然现在在我国正歌剧创作中,用现代技法都不多,基本上都是浪漫主义时期或民族乐派的那种有调性的音乐。但是旋律不堪入耳,演员唱起来也很困难,观众听起来也很困难,记不住,所喂口水歌。就这些东西是中国歌剧的大敌,现在好像还没有引起相关的主创人的重视。当然很好的作曲家也有,像金湘创作《原野》的时候;徐占海创作《苍原》的时候;莫凡创作《雷雨》的时候;还都是可以的,他们的创作都比较认真,但是这样的作曲家比较少。像王祖皆、张卓娅夫妇他们的创作态度是相当严肃的,所以才能出好作品。但有一些人才华一般,还要和莫扎特比,多长时间就能写一部歌剧,这怎么行呢!还有一些人仅仅就弄一个旋律,有一个作曲团队帮他搞配器,接到的委约很多,也来不及仔细推敲。就不得不交稿。因为首演的时间已经定了,某年某月某日,在某某地方首演,你必须在某一时间前交稿。时间已经定了,如果不交稿,就逼着他交稿。这种情况有很多,所以关键是我们讲了许多评论家如何影响评论的。创作家除非你评论他的作品,否则他不看评论。你评论他的作品,除非你批评他,他才予以重视。而且常常不服气。现在,许多作曲家,创作家不看评论。这也是一个问题。
杨柳成: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生都是90后,他们都生活在一个被流行音乐包围客观环境中,他们中很多也很喜欢流行音乐。那流行音乐应不应当评论?如果要评论的话,该如何切入?
居其宏:流行音乐当然可以评论。流行音乐在大陆才三十年,抗日战争时期它受到左翼音乐家们的批判,认为它是“商女不知亡国恨,隔江犹唱后庭花”。这个批评有没有道理?有一定道理。但是,我觉得,也没有道理,为什么呢?因为即便在那个时候,人们也依然需要爱情,依然需要休养生息,依然有男欢女爱。所以鲁迅曾经批评一些人,把什么都跟抗战联系起来。说吃西瓜的时候,一切西瓜吃下去,帝国主义瓜分中国,这个西瓜都不能吃了,好像抗战就不能吃西瓜了,这个就过分了。当然,全国解放以后,我们流行音乐是全面的禁止,连抒情歌曲也不行。改革开放初期,邓丽君的盒带传入大陆,慢慢的才有流行音乐影响到大陆。中国的流行音乐也是受到当局的严厉批判和禁止的,公安部曾经和中国音协曾发布一个公告:“流行音乐一律禁止”,在社会上禁止是不太可行的;后来退一步,流行音乐不准进课堂,也禁止不了。所以在八十年代的时候,我们这一代人,是在三条战线上作战。 一条战线就是思潮思想,指导思想,中国音乐发展的指导思想领域;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线是现在新潮音乐的战线;第三个领域就是流行音乐领域。当时主要的论战对象就是对于一些中国音协的老同志,包括吕骥先生是我的导师,包括赵沨同志,都反对流行音乐,我们就要为流行音乐在大陆的生存权发展权,进行论战。公开发表在刊物上。这个论战必须牵扯到一些实际的作品。当时大陆有一批作曲家,像王酩是写了一个《妹妹找哥泪花流》,他们批判名义上写兄妹,实际上写爱情,写爱情也是不行的。对于这方面,我们就跟他们进行争论,为什么不能写爱情?包括后来谷建芬的作品、王立平的作品、后来有个湖北写《王昭君》的,包括李谷一的气声唱法,都受到了当局的严厉批判。我们当时就坚决维护这些创作家、演唱家,创作和演唱这些流行歌曲。这些论战其实也是评论,就是围绕某一个题材,已经出现的题材,否定他的意见,跟他针锋相对进行论辩,也是一种评论。发展到后来八十九十年代以后,流行歌曲的合法权益已经没有问题了,再也没有人会说它是资产阶级的,腐朽的,没落的了,产生了许多好作品,比如广东的音乐家李海鹰写的《弯弯的月亮》。我在《共和国音乐史》里面写,八九十年代以后的流行音乐,我比较看好的一个就是这个《弯弯的月亮》。还有刘欢他自己写自己唱的,比如说《千万次的问》,还有一个历史剧《胡雪岩》里面的插曲,运用了一个京剧的音调等等。包括王立平写的《红楼梦》里面的《枉凝眉》、《葬花吟》,都是十分不错的。还有“西北风”的音乐,也是被充分加以肯定的,比如《月亮走我也走》。我觉得一个艺术家,尤其是搞史学的评论家,你可以有个人的喜好,但是在你学术著作里面或者评论作品里面,你不能偏于个人的憎恶,应当从整个的艺术大势出发,对别人进行评价。你只能说这个作品好不好,不能说这一类体裁不行。题材雅有雅趣,俗有俗趣,各有各的美。过去我们是封建时代从雅避俗。雅的高雅,俗的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。共产党人以后把这个改过来了,但是又发展到另外一个方面,从俗避雅。革命群众歌曲好,交响乐钢琴曲,室内乐,艺术歌曲不行,这就是另外一个极端。今天我们这个自由社会就允许各类体裁,自己按照自己的艺术规律去发展。古代还有所谓高山流水和者甚少,下里巴人和者甚众,更何况今天呢。今天为人民创作的导向,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。我写过一篇文章,人民也是多层次的,你是人民,他也是人民,我也是人民。马克思说过,对于非音乐的耳朵再好的音乐,也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音乐要懂的。所以说像现代音乐,尤其像很尖锐的现代派音乐。我本人不喜欢,但是我认为它有它生存的权利。在我们为人民而创作的过程中,它也是一员,必须保护它的生存权利。但是你可以对其中某个作品全盘否定它,这个作品写得不好是可以的,你不能否定这个体裁本身,这一类风格本身。谭盾的那种《秦始皇》,周龙的《白蛇传》,郭文景的《骆驼祥子》这样的作品,一般的老百姓是不会看的,像我们这些搞歌剧的人是必须要看的。要发现他们其中的一些好东西,要不要存在?允许它存在。但主体还是正歌剧。正剧更多的不是用现代技法写的,是用古典派、浪漫派、民族乐派,借鉴一点现代技法写的。但是作为一种个别特殊需要的时候才采用。一般情况下都是有调性的,讲究戏剧性,讲究对比,讲究结构的完整,讲究旋律的优美动听。
还有音乐剧,在欧美主要是给年轻人看的,仍然是雅俗共赏,老少皆宜的。去年我去了英国伦敦,看到了两部音乐剧。当然,年轻人是主体,但是也有各个年龄层次的人,也有各个阶层收入不一样的群体。作为一个理论家,有个人的喜好是必然的。不可能没有个人的观点,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。但是作为一个理论家,出现在公共话语空间的时候,你就不是再代表你个人,而是你要代表一个科学公正的,站在一个更宏观的立场上来看问题,所以我觉得流行音乐也是这样,当然流行音乐发展到新世纪以后也有很多。我的主要研究方向还是在歌剧、史论等方向,间接研究到中国近现代史,也研究音乐批评,音乐美学,研究得比较杂。我的确不喜欢现在的流行歌曲。但是我不发言,因为我没有研究。要了解流行音乐,流行歌曲方面的批评的话。建议找一下金兆钧,他是这方面的权威。因为我的主要研究不在这一块,当代的流行音乐,尤其近几年的,我说不出任何意见。仅仅只是偶尔,在电视里面听到。


访谈现场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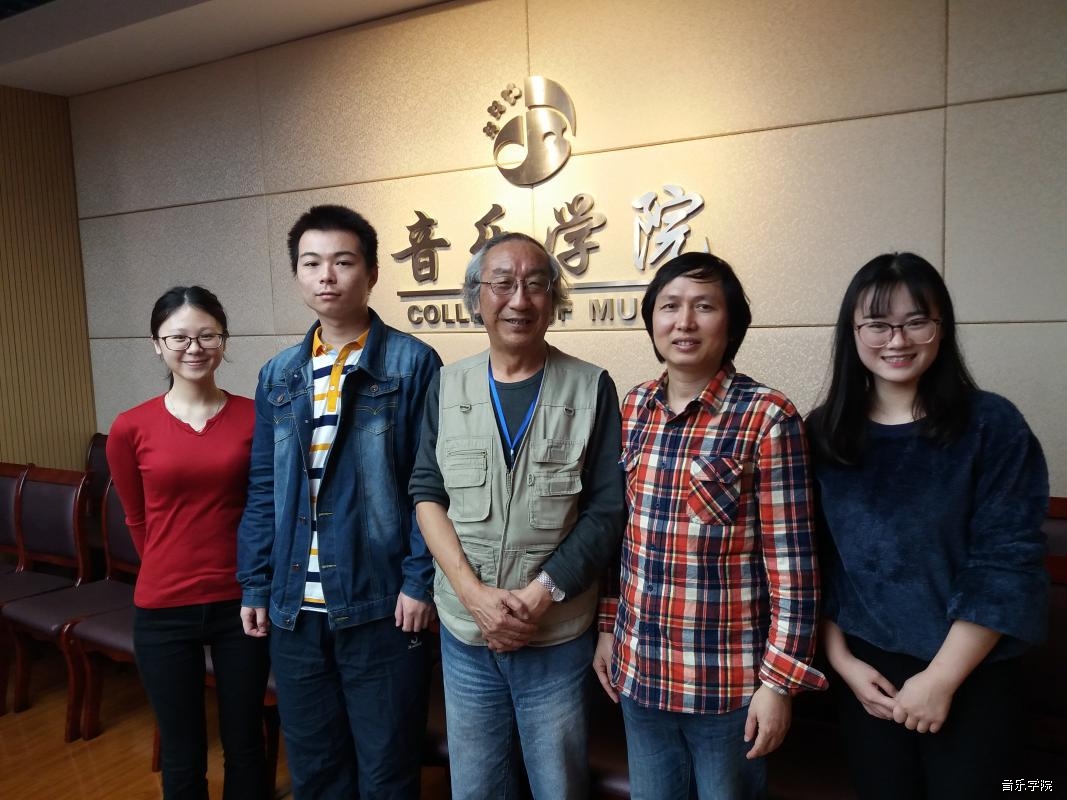
合影留念
音乐学系供稿:记者/杨柳成,记录及整理/于跃,摄影/潘林紫

